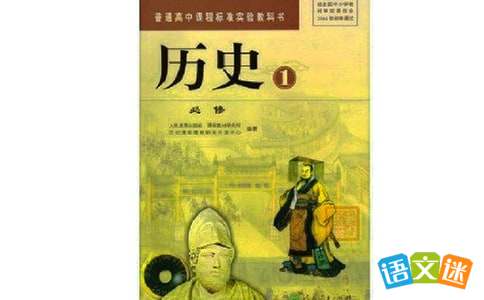熟悉的人都说,张建是个有福分的男性。他妻子刘艳钻营着一家规模很大的私人医院,是出名的铁娘子。张建不用工作,每日就是看看书,喝喝酒,遛遛家里养的大丹犬。有人说他是劫后余生,必有后福。十几年前他曾遭遇过一次严重车祸,但除了给他脸上留下条伤疤和间歇性的头疼外,并没有造成大的伤害。从那今后,妻子更是啥都不让他干了,干脆连车都不让他开,给他雇了个专职司机。
但最近张建有点郁闷,他常常做一个离奇的梦,极其传神。梦里他沿着一条弯弯曲曲的小路,走过一个池塘,池塘边有一个孩子在喊他。他听不清喊什么,但能感受到,那孩子喊得很亲切,他心里也以为很亲切。又走了一会儿,他穿过几间平房,来到一处小屋前。比起周围的屋子,这间屋子显得有些破旧。一个女性在院子里洗衣服,不算美丽,但看起来很温柔贤惠。女性瞥见他,站起来擦擦手,笑着迎向他。然后他就醒了。
这个梦每隔两三天他就会做一次,并且一次比一次清楚。一个月后,他已经能在梦里看到路边的界碑了,虽然看不清界碑上的字。他还隐约听见孩子喊的是个很短的词,而那个女性洗的是一件劳动布做成的衣服。
张建跟妻子说了自己的怪梦。刘艳听后哈哈大笑:“做梦也能把你苦恼成这样啊。”张建说:“那梦太传神了,我一辈子都没去过那种偏远农村,怎么会有这么传神的梦呢?”刘艳笑着说:“没事,我让人给你开点安神药,吃了就好了。”
当天晚上刘艳就拿回来一瓶药,张建看瓶子上啥也没写,就问:“这是啥药啊,连个包装也没有,我一次吃几片?一天吃几回?”刘艳说:“这是进口药,包装比药都贵。你晚上睡觉前吃,一次一片就行。”
张建吃了安神药之后,果真没再做那个怪梦,并且连梦都不做了。刘艳告诉他,人会做梦是因为大脑不能完全休息,吃了安神药后大脑完全休息了,自然就没梦了。张建以为这药虽然好使,可有点副作用,让人注意力不集中,白日有时也有点迷含糊糊的。刘艳说:“这药刚吃是这样,吃几天适应了就好了。”
张建反倒有点怅然若失,几天不做梦,他却有点想那个梦里的孩子和女性了。于是他决定停药,看会不会再做那个梦。第一天大概是另有残余的药性,他没有做梦。第二天他果真做梦了,并且这次的梦比之前的更传神,更清楚,他明显地瞥见界碑上写着“陈家屯”三个字。并且那个女性洗的衣服,是一件劳动布做的夹克衫。
张建把自己的新发现告诉了刘艳,不过他没敢告诉刘艳停药的事,怕她气愤。刘艳面色有些繁重了:“梦的细节越来越多,说明你的大脑编的故事越来越复杂,这样下去会精神割裂的。”张建吓坏了:“那怎么办?”刘艳说:“你加大药的剂量吧,一次两片。”
张建说:“但是我怕药的副作用太大了。”刘艳笑着说:“你忘了我是大夫?”张建说:“你是大夫,可你主修的是整形专业,对脑筋的事,你行吗?”刘艳说:“就算我不行,我手下那么多大夫都是高手,他们敢给老板的丈夫乱开药方吗?”
刘艳说的有道理,张建也就听了。不过他没吃双份,横竖一次一片就不做梦了。
虽然不做梦了,但张建以为这个传神的梦很有趣,决定把它画出来。拿起笔来才知道,自己的画画水平实在不行。他想横竖也是闲着,干脆学学画画吧。
张建请了一个大学美术系的学生当家教。刘艳问他为啥忽然想学画画,张建说闲得无聊,刘艳又不让他工作,总得有点喜好吧。大学生教得挺当真,无奈张建的悟性实在太差,学了一个月也没什么进步。他急着想把自己的梦画出来,非常烦恼。大学生说:“学画是急不得的,您这么着急,是要做什么吗?”张建有点不美意思地把自己的梦说了一遍,然后说:“我就是以为这梦有趣,想把它画下来。我此刻正在吃药诊治,也许今后就不会再做这个梦了,留个怀念。”
大学生说:“这好办,你说,我来帮你画。哪里过失你随时指出来,我修改就是了。”张建惊奇地说:“能行吗?”大学生笑了笑:“我学的是写实类的画法,相信画你的梦不成问题。”
张建以为这主意良好,就开始实施了。他把自己的梦讲给大学生听,大学生果真水平非凡,那弯弯曲曲的小路、池塘,都画得像模像样。人物难一些,张建表达才能一般,不能把那个男孩和女性的模样特征描述得很明显。好在两个人有富足的时间,张建一点点说,大学生一点点改,居然也画出了七分相似。
大学生边画边说:“看来您真的对农村很认识,有些细节没去过农村的人很难想象出来。这景致简直和我老家那一带的景致太像了。”张建苦笑着说:“可我确实没去过农村。我在城市出生,在城市长大,独一的农村经验也就是节假日到郊区的农家乐吃个饭。”他看着画说:“对了,这路边另有块界碑,上面写着‘陈家屯’。”
大学生愣了一下:“陈家屯?我家是柳树县王家屯的,柳树县另有个陈家屯。不会这么巧吧?”张建也很惊奇:“柳树县在哪?”大学生说:“离这里不算远,五百公里。”张建想了想说:“这样吧,你暑假回家时顺便去陈家屯看看,盘缠什么的我给你报销,怎样?”大学生说:“没问题,我也想看看是不是这么巧。”
暑假到了,大学生走了,张建坚持吃药,也不再做梦。生活回到了正轨。
然而这种安静的生活在一个月后被打破了。大学生从家乡回来了,张建发现他的神情很离奇,既高兴又有点畏惧。他拿出几张照片给张建看,张建看完后也傻眼了。
这些照片是大学生在去陈家屯时拍的,从一进村庄开始拍,有十多张。那山,那树,那路,那池塘,那界碑,那平房,都无比认识。唯独匮乏的是孩子和女性。大学生说:“你看到的那家平房,我去那天没有人,邻居说走亲戚去了。我问家里有什么人,邻居说是一个寡妇带着一个儿子,儿子今年上大学。”
送走大学生,张建把照片藏了起来,他不想告诉刘艳,因为他以为刘艳不会相信,没准还会给他加大药量。
过了几天,张建跟刘艳说想出去玩玩。刘艳说自己医院的事太忙,仍是等等吧。张建说:“没事,此刻旅行团利便得很,我自己跟团出去好了。”刘艳说:“我不太定心,车祸后你常常头疼,另有精神割裂的迹象。假如你实在想玩,仍是筹划好去哪儿,让司机开车带你去吧。”
张建试探着说了一个地方,跟柳树县一个方向,刘艳说:“不行,不能往北边去。那里风沙大,对你身体不好。”张建说:“此刻是夏季,北边凉爽啊。”刘艳说:“海边也凉爽,并且对你身体有好处。去南方吧,我给你安排路线。”
张建很郁闷,但他不敢反对,妻子在家里说一不二。他更不敢说自己是要去看梦里的地方,妻子不会相信这么灵异的事,没准直接断定自己精神割裂,就更糟糕了。
收拾好东西,带着刘艳的嘱咐和药,司机拉着张建上路了。出城后,张建说:“掉头,去柳树县。”司机吓了一跳:“张总,这可不行啊,刘总让我严格按规定路线走,您谅解谅解我,万一让刘总知道了,可就砸了我的饭碗啊。”张建说:“你不说,我不说,谁也不会知道。回去买两张那个城市的住宿就行了。”看司机还在踌躇,张建沉下了脸:“你冒犯了我,我一样可以砸你的饭碗,你信不信?”
张建平时性情很好,这忽然一发威,确实把司机吓住了。司机想,人家两口子,床头打斗床尾和,自己何须死心眼。于是调转车头,直奔柳树县而去。
中午到了柳树县。司机根据导航顺利地从柳树县城开到了陈家屯。到了屯子口,张建让司机把车停在村外等着,自己下车步行进村。
进村的路是弯弯曲曲的土路,和张建在梦中见到的一样。没走几步,张建就看到了路边的界碑,粗拙的方石上刻着“陈家屯”三个字,和他梦里的一模一样。
张建蹲下来,抚摸着这块界碑,心里说不清是什么感受。惶恐、惧怕、暖和、认识,都有。他站起来,沿着小路继续向前走。
他瞥见了池塘。池塘比梦中的小了,水也少了,里面丢了好多杂物。但他仍能认出这个池塘,虽然池塘边没有那个冲他喊的孩子。他站了好久,才继续往前走。
梦中的平房只剩下少数几家维持原样,其他的都翻盖过了。在原本是空隙的地方,也盖起了不少屋子。但路没变,他仍旧能顺着梦中的小路向前走。
终于走到了梦中的平房前,屋子没有变化,院子也没什么变化,只是一些东西没有梦里的新了。那个用杆子竖起来的电视天线很破旧了,而在他梦里仍是新崭崭的。院墙没变,只是路过风吹雨打变矮了些,能瞥见院子里的一切。院子里没有女性洗衣服,但靠墙边有个大木盆,已经腐朽,不能用了。
他站在大门前踌躇了一下,终于伸手推开了门。屋里走出来一个小伙子,嘴唇上已经有了胡须,但脸上稚气未脱。他问张建:“请问您是……”张建张张嘴,不知道该说什么。他总不能告诉人家他梦见了人家的家吧。他灵机一动说:“我找爸,我小时候在这个村庄里住过,是爸的密友。”小伙子说:“我爸爸已经归天十几年了,叔叔请进屋吧。”
张建随着少年走进屋,一个女性从里屋迎出来:“谁来了?”女性的变化没有少年的大,比起梦里,她只是脸上多了些淡淡的皱纹,头发依然是乌黑的,依然温柔娴静。张建把自己的假话又说了一遍,女性轻声说:“陈龙走了十几年了,让你白跑了一趟。”
张建说:“我能给他上炷香吗?”女性点点头,带张建走到一个小屋里,屋里放着些杂物,在桌子上摆着一张照片,旁边有个小香炉。张建看着黑框里的相片,突然产生了一种奇特的感受:只管面前是一张完全生疏的脸孔,他却感受无比认识。难道自己真的熟悉这个人,而自己却忘了?
张建留在陈龙家里吃了晚饭。他让司机去县城用饭,晚上来接他。席间,他用着粗瓷的碗碟、毛竹的筷子,暖和认识的感受又一次涌上心头。他吃着饭菜,看着房子,感受就像是一家人。
他踌躇好久,终于问出了心里的问题:“陈龙是怎么死的?”女性低着头说:“车祸,十几年前,他进城打工,结果出了车祸,急救无效死了。当时就像天塌了一样,孩子还小,亲戚离得都很远,也照顾不到。假如不是殡仪馆的馆长好心,免了我们的火葬费,还给了我们盘缠,我大概都没法把骨灰带回来。”
张建问:“他在哪个城市打工?”女性说出后,张建愣了,那正是他栖身的城市,又问了时间,正好是他出车祸的时候。他突然想起了在杂志上看到的一个故事。
外洋曾经有过一个案例,两个生命垂危的病人,在同一间病房里,其中一个先死了,另一个则在垂危中被救了回来。结果诡异的事发生了,被救活的人坚称自己是死掉的那个人,并且对死去之人的家庭出身洞若观火,甚至连伴侣间的私密都说得一点不差。这桩借尸还魂的事引起了极大轰动,两个家庭都争这个人。有医学家以为人的思维会以脑电波形式发散,所谓心有灵犀就是俩人的脑电波频率邻近。垂危之人脑电波很弱,轻易受滋扰;而人临死时脑电波是最强的,因此垂危之人的脑电波被临死之人滋扰了。但也有医学家以为脑电波之说虚妄,真实原由应该是这两个人长时间在一个病房里,不免互相攀谈,相互对对方的出身家庭都很了解。濒死复活的人,本就神志恍惚,把别人的生平经历当成自己的,也是有大概的。
但是,张建据说自己出车祸后一直昏厥,不应该跟别人攀谈过。莫非自己曾和陈龙在一个病房,陈龙临死前的脑电波影响了自己,自己才会有一部分他的记忆?
张建知道自己出车祸后是在妻子的医院急救的,那么陈龙是在哪里急救的呢?他询问那女性,女性也说不清。她当时还年青,初到大城市摸不着北,加上伤心过分,基本什么都不记得了,独一记得的就是热心资助她的殡仪馆经理叫谷峰。
张建给女性留下了一些钱,女性死活不要,张建说:“我和陈龙是儿时挚友,这是我的一点心意,况且孩子读书需要钱,就别推辞了。”女性这才收下。司机来接张建,张建上车后说:“连夜回家。”
到家已经是第二天早上了,张建直接去了市里最大的殡仪馆,询问经理是否定识谷峰。经理说:“他是咱们市第三殡仪馆的经理。”
第三殡仪馆是本市规模最小的殡仪馆,收费相对也低廉。谷峰五十多岁,他热情地问:“有什么需要效劳的吗?”张建说:“我有个密友当年是在您这里办的后事,我想查一下他的档案。”谷峰点头:“没问题,这是我们服务的一部分。您说一下姓名和大体年份,我来查。”
张建拿到了陈龙的档案,里面有身份证复印件,和陈龙家摆的照片一模一样,尸体来历一栏里写的是市第一医院,和自己不在一家医院。灭亡原由是车祸脑损伤。张建叹口吻,看来这事是很难诠释了。他谢过谷峰,回家了。
刘艳见他提前回来了,很意外。张建说太长时间不出门,不习惯,仍是等刘艳不忙时一起出去玩吧。刘艳很兴奋,拉着张建出去吃西餐。
晚上,张建拿起刘艳给他的药,想了想,扔进了马桶。回屋时,刘艳问:“吃药了吗?”张建点点头。
张建的司机回家乡成亲去了,刘艳又给他找了个新司机。新司机比较健谈,和张建处得良好。一天他们开着车去郊区玩,新司机说:“我一年的工资都买不了您的一个车轱辘。”张建笑了:“没那么浮夸吧,这车一共也就一百万,轱辘能值几许钱啊。”新司机叫起来:“一百万那是裸车,您这车但是顶配,导航都带主动防盗功效。”张建愣了一下:“什么叫主动防盗?”新司机说:“自动定位啊,可以预先设定路线,一旦偏离,车就自动通知车主。”
张建脑壳嗡的一下:这么说,自己去柳树县的事刘艳早就知道了,以她的性格,怎么大概一句话都不问呢?
张建停药十天了,他又开始做那个梦。细节越来越清楚,但没有更多内容。他想去办点事,但他没法支开司机单独行动。终于有一天,车在路上被人追尾了,要送去修三天。张建放了司机的假,然后打车出发了。
他先去了第一医院,查找陈龙的档案,然后给刘艳打电话,约她一起吃午饭。他躲在医院外面,看着刘艳出发后,就跑进医院的太平间。值班的人熟悉他,赶快打招呼:“张先生,您来了?”张建说:“刘院长在这儿吗?我听说她要来检查。”值班的人说:“没有啊,昨天刚检查完。”张建装作不在意地问:“咱这太平间的寒气不行啊,这么热。”值班人说:“横竖尸体也放不了多久,没事。”张建心怦怦跳:“那尸体送哪去啊?”值班的人随口说:“第三殡仪馆啊,咱医院是他们的大客户。”
张建去了刘艳的办公室,这里有一台电脑,张建以前听刘艳说过,她能通过这台电脑监控所有病房和科室。他希望这里有他需要的东西。他拿了一个大容量的U盘,把所有能拷的东西都拷了下来,然后就去找刘艳了。
中午用饭的时候,刘艳一直看着张建,看得他心里发毛。
张建下午在家里开始了艰辛的查找工作。由于不认识医院的数据库,他查不到任何东西。他突然开始猜疑,自己是理工科结业生,怎么会对电脑这么生疏呢?车祸之后,自己仿佛什么都不会干了。刘艳说是恢复得不好,什么也不让他干。十多年了,自己就像个酒囊饭袋一样过日子,平时感受不出问题,此刻才发现,自己什么都不会了。
张建跑到电脑城,花三千块钱让一个小青年帮他从数据库里查资料。小青年折腾了一个小时,查到了陈龙的医疗记实,看起来没什么问题:车祸,医治无效,灭亡。当他查到自己的医疗记实时,惊奇地发现,居然和陈龙在同一天。
也许这就可以用脑电波理论来诠释了,但为什么殡仪馆要骗自己?张建突然看到了医疗记实中的一项,他当即上了出租车:“第一医院。”
当天晚上,张建又做梦了,和平时一样,他梦见自己走在那条小路上。但和以往区别的是,他的脚步越来越繁重,险些都走不动了。他走过池塘,那个孩子冲他喊,这次他听到了,孩子在叫“爸爸”。他继续走,走到了那个院子,那个女性在洗衣服,但他的脚步太繁重了,他没法接近。女性站起来,他忽然发现女性的脸变成了刘艳,正看着他冷笑。
张建惊醒了,面前是刘艳冷笑的脸:“这么说,你醒了?”张建点点头:“我醒了,我就是陈龙吧?”刘艳说:“你什么时候知道的?”张建说:“我拿到第一医院的出生记实,出生记实上写着张建的血型是A型,可我的血型是O型。除了出生记实之外张建的所有医疗记实都在你的医院里,你都改成了O型。”
刘艳说:“十几年了,我原来觉得不会有变故。可从你跟我说那个梦开始,我就知道会有今天。我让谷峰变动档案,原来觉得你会死心,没想到你仍是不罢休。那天中午,你一进餐厅我就闻到你身上的味了。没有哪个大夫比我更认识太平间的味道。”
张建说:“其实火葬的是张建,对吧?你为什么要把我变成张建?”
刘艳说:“我辛苦创业,张建却在外面找小三,还诡计分我的财富。医院是我的命,我是不会分给他的。恰好,你呈现了,车祸把你撞得面目全非,但你的身段和脸型都很像张建。你是晚上送急诊的,只有我在值班。我把张建骗到医院,用镇痛剂了他,砸烂他的脸,他就成了你的替死鬼,进了谷峰的焚化炉。对别人而言,你出车祸,急救无效死了;而张建还躺在病床上等候救治。”
陈龙苦笑着说:“莫非把我送到医院的人就那么好骗?你干吗不干脆让我也死掉,岂不更无后患?何苦要急救还要整容,费这么多事?”刘艳说:“张建假如死了,我又没有特别传神的车祸现场,很轻易招惹警方猜疑。但假如张建活着,那就不会有人调查了。你知道张建为什么要和我离婚吗?因为我不能生育,我多希望能有个好男性陪着我,不然我只能孤零零地过一辈子。我听到你昏厥时的呓语,我以为你是个善良的好男性。至于送你来医院的人,预计就是肇事者,他把你扔在医院门口就跑了,没人追究他,他莫非还会回来多事?”
陈龙说:“张建的记忆,都是在我恢复过程中你灌输给我的吧。我失忆了是吗?”刘艳说:“你有大概失忆了,但还不够彻底。我当年学美容时对神经类药物进行过研究,你吃的药其实是我自己配的,在急救你的过程中也大量使用过。这种药能强力毁坏人的远期记忆力,但对近期的记忆损伤不大。我清空了你的记忆,在给你诊治的过程中把张建的事说给你听。人的大脑是很希奇的,尤其是受过创伤的大脑,常常分不清什么是真实的记忆,什么是虚假的记忆。”
陈龙长叹一声:“我的老婆和儿子这些年过的是什么日子,你知道吗?”刘艳说:“我知道,我一直关注着他们。你觉得假如没有匿名捐赠,她能供孩子上大学吗?我要求不高,只求有一个善良的男性陪着我,哪怕我养他一辈子都行,这要求过度吗?”
陈龙说:“可你不该抢别人的老公。”刘艳说:“假如不是我尽力急救你,你早就死了,你的命是我给的,我不能要点回报吗?”陈龙缄默了,刘艳说的确实有道理,但是,他不能健忘自己的家。刘艳哭了:“你为什么一定要追查到底?像之前那样过日子不好吗?”
陈龙摇摇头:“不大概了,已经回不到之前的样子了。你仍是让我走吧。”
刘艳擦干眼泪,说:“你带着这样一张脸回去,你的妻子孩子会认你吗?”陈龙愣了一下:“我可以诠释。”刘艳摇摇头:“不,你不能诠释,那样就会牵出张建的死因。你是我的老公,永远都是我的老公。”
陈龙想坐起来,却发现身上发麻,使不上一点气力,他明白了:“你给我下了药,是吗?”刘艳说:“只是神经麻木类的药物。假如我们谈得好,原来我是不想用下一种药的。但是……”
刘艳拿出一个小瓶,放到陈龙嘴边,温柔地说:“亲爱的,我不会健忘你的。”陈龙突然笑了:“十几年前,张建替我死了,今天,轮到我替他死。在这十几年捡来的命里,你对我很好。”他张开了嘴,把药都咽下去了。然后,他以为面前越来越黑,只瞥见刘艳满是泪水的脸在面前晃动……
陈龙醒了过来,他很意外,他本觉得自己再也不会醒了。然后他瞥见桌上放着一封信。
“亲爱的,我去自首了。昨天给你喝的药,是我最新研究的,也许能恢复你的记忆,也许不能。这是我独一能做的了。人做错了事,总要付出代价。其实我在十几年前就错了,我应该脱离那个不爱我的男性,而不是杀了他。此刻是我付出代价的时候了。谢谢你,让我这十几年过得很幸福,虽然,那份惭愧一直煎熬着我。此刻我的幸福结束了,煎熬也结束了。我已经写了遗嘱,把所有财富留给你。替我向你的爱人和孩子说声对不起。爱你的老婆。”
陈龙把信揣进怀里,收拾了一点东西,锁上了门。
他要回家了。